
| 服务热线: 13384778080 |
 |

| 服务热线: 13384778080 |
 |
来源:新京报网 |
关键词:刘亮程 散文 一个人的村庄 |
发布时间:2019.01.10 |
在刘亮程看来,小说家也是捎话人。当我们看懂或者理解了一段远去的生活,把这段生活呈现给今天的人们的时候,也把历史深处的声音捎给今天的人。
刘亮程以散文成名。《一个人的村庄》让人们看到一个荒凉又丰富的乡村,在那里,人畜共居,狗、驴、马与人齐平,乃至一阵风、一场雨皆有来由,皆有生命。那是作者的成长之地,也是他形成自我之地,是他的根。他以文字之真、情感之真写个人的历史与现实,塑造自己的同时又触动他人,赢得“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”的名声。
散文的要义是真,而在从真走向虚构的过程中,刘亮程的“散文节奏”一直强烈地存在着。《虚土》和《凿空》是小说,却有着作者散文的强大引力,故事讲的也是村庄的生存之状,其间的人事与自然。到了最新作品《捎话》,刘亮程从散文中彻底走出,进入了纯粹的虚构。当然,他带有诗意的文字还在,毛驴的角色依然重要,但世界已非读者熟悉的他的那个世界。
《捎话》的故事背景在古代,情节说来简单:一人一驴,穿过战场又回来。但故事当然又没那么简单。两个国家,毗沙和黑勒,因信仰不同而开启长达数十年的战争,两国间书信断绝,无法沟通,捎话人应运而生。这是本书的主题,指向“语言之难“,语言的无法交流。但在现实中,语言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即是交流。这是悖论。刘亮程说:“语言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工具,它一手挖洞,去沟通,一手在垒墙,在隔绝,这就是我理解的语言。”
此外,作者讲故事置于战争这一极端环境中,想要做的并非仅仅是去反思战争。与平静岁月不同,在战争中,生死仅一线之隔,对生与死的思考才是作者想要的。

刘亮程,中国作家,新疆人。著有诗集《晒晒黄沙梁的太阳》,散文集《一个人的村庄》《在新疆》,长篇小说《虚土》《凿空》等,有多篇文章收入全国中学、大学语文课本。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。2013年入住新疆木垒,创建菜籽沟艺术家村落及木垒书院,任院长。
新京报:先请你谈一下写作《捎话》的缘起吧。
刘亮程:《捎话》这本书写的是一千年前的一个故事,主题是“语言之难”,语言交流之困难。这些年看历史多,我喜欢盯着某一段历史看,想看懂它。《捎话》所捎来的,是千年前已经湮灭、埋于尘土之下又被重新唤醒、被一部小说捎带到今天的众生之声。在这样的声音中,有人的精神之变所带来的痛,有人的声音,也有人之外的其他生命和非生命的声音。所以,它也是一部众声喧哗的书。
小说家也是捎话人。当我们看懂或者理解了一段远去的生活,把这段生活呈现给今天的人们的时候,也把历史深处的声音捎给今天的人。我也认为,历史从来没过去,历史是我们现在的镜像,或者现在的生活只是历史生活的一个影子。它们在相互映照。这是我写作这本书的一个动因。
新京报:这本书的大背景是战争。在现今的文学作品中,对战争的反思好像不多。你把本书的背景设置为战争,有哪些考虑?
刘亮程:现在作家书写战争题材的非常多。解放战争、抗日战争以及二战,还有历史上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战争,都被作家书写。许多作家乐于书写战争,因为一部战争题材的小说会让故事变得非常好看,作家也会在战争的惨烈中,去完成人物的命运。反思战争也好、揭露战争也好、呈现战争也好,战争总是作家乐意去写的。
《捎话》中的这场战争,没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呈现,它是一场荒谬的战争,一场影子之战。这本书的源起是,东边的毗沙国修了一道高高的院墙,把远在千里之外的黑勒国早晨的阳光挡住了,战争就这样开始了。但真实的原因是,两国开始信仰不一样的宗教。战争的这种荒谬性,并不能削减战争的惨烈,任何一场战争,不管起因是什么,一旦开始,它都是一个收割人头的机器,所以《捎话》呈现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,故事也在战争中铺开。
但是,所有的战争,你看完之后,你会觉得它如此真实,又如此的不真实,它是荒谬的,它没有意义。它唯一的意义就是,作者在书写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那些生和死的意义。所以,这部小说的主题也不在于书写战争,它通过书写战争去呈现作者所思考的生和死。这是这部小说想要呈现的。

《捎话》 作者:刘亮程 版本:译林出版社 2018年11月
新京报: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、迷人的角色“毛驴谢”,它可以听到、看到很多人所不能见的东西。在你之前的作品中对驴的描写也很多。为什么会对驴如此偏爱?通过塑造这一角色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?
刘亮程:“毛驴”一直是我文学作品中的重要角色。从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开始,毛驴这个形象就不断出现在我的散文和小说中。我喜欢驴这种动物,因为它不同于别的动物,我感觉到它有神性,在民间传说中也有“驴鬼得很“的说法,驴是半个鬼。我平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毛驴,也觉得看不透它,毛驴经常会斜着眼睛看人。我认为,毛驴是一种半驯化的动物,它当然完全被人驯服了,给人当牲口,但是它经常会用自己的倔强对人发脾气。我老是觉得这种动物有思想,它会揣摩人,它顺从的同时也倔强。它也知道,人接受它的顺从,也会接受它的倔强。这种毛驴精神让我看到了一个动物在人世中生活的策略,它是有精神的,有灵魂的,有思想的。
所以,我一直把这样一种动物安置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,是在我的文学中安置一个人之外的其他生命的眼睛和心灵,让这颗心灵从另一个角度、另一个方向感受和感知这个只有单一的人的目光和思想的世界。
新京报:书封上有四个字“万物有灵”,你的写作也确实呈现了这个词所表达的状态,形成这种思想受到了哪些影响?
刘亮程:可能跟生活有关系。我从小生活在乡村,从小就在乡村万物中长大,能够更多地去贴近或者感受人之外的其他生命和非生命。现在我回想起小时候,更多会想到的是包围村子的草木、荒野,我会更多回想到一年四季刮过村庄的风和它带来的声音,在风声中尘土的声音、木头的声音、屋檐的声音,还有天空的声音。
在这样声音的记忆中,我天生地就会感知到所有这些有声音的生命都是有灵魂的,因为我能听见它,我听见它的时候,它是一个生命或说一个灵魂在发出声音。这是我对万物有灵的一种个人感受。这样的感受也不断地被我得以加强,书写在我的文字中,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书写方式。
新京报:关于这本书不得不提的一个问题,就是“语言”。在日常生活中,语言被我们用来交流、沟通,打破障碍,但如你所说,“语言是另一重夜”。它本身即是障碍。你如何看待这个悖论?
刘亮程:我是一个使用语言、用语言创作的人,语言是我唯一的表述工具。但是,当你用语言去描述事物的时候,当你试图通过语言达到某个层面的时候,你会发现语言的无能为力、语言的隔障。语言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工具,它一手挖洞,去沟通;一手在垒墙,在隔绝,这就是我理解的语言,一个写作者心中理解的语言。
新京报:这部小说和传统的长篇有一定的不同,你是如何结构这部小说的?像是片段的连缀,但每个片段又有内在的连贯性。
刘亮程:这部小说的叙述方式,天生就是为我所讲的这个故事所生的。一部小说如何去讲、如何去结构,可能都有一个最适合这部小说的形态,就像我们为一个心灵找到一个身体一样,小说的形态就是这部小说灵魂的一个外貌、一个外形。它只能长成这样。这部小说因为有这样一个故事,有要表述的这些内容,它就天然地有了这样一种形态。只能这样去解释。
传统长篇小说千奇百怪、样式繁多,《捎话》有它的不像之处,可能也有像之处。它就是一人一驴穿越战场,再从战场回来,走了一个回头路,然后小说就完了。关键是,发生在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小说线索中的那些完全不一样的东西,才是这部小说要说的。小说故事只是一个引子而已,引导作者去完成比小说故事更重要的背后的故事。这就是我所说的,故事要捎带故事,一个故事把另一个故事捎带出来。
新京报:你以散文成名,后来开始写小说,你觉得散文和小说的写作有哪些不同?在这种文体的转换中有困难吗?
刘亮程:我对文体没有自觉的意识,至少在我前期的写作中,我一直都不在意文体的。我写《一个人的村庄》的时候,我也不认为我在写散文。事实上,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刚出来的时候,也有评论家把它当作小说去研究。《一个人的村庄》每篇单看可能都是散文,整体看,它或许也是小说,因为它有一个贯穿始末的主人公,就是那个第一人称的“我”。这本书写了一个人,写了一个村庄的命运,它是散文吗?也没有这样的传统散文。

《虚土》 作者:刘亮程 版本:果麦文化 |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12月
后来写《虚土》的时候,我也没有把它明确当成散文或者小说去写,只是把它写完了。写完后,出版社说这是小说,我说那就当小说发吧;后来再版的时候,另外一个出版社说这应该是散文,我说那就当散文发吧。所以,《虚土》当小说出版过一次,当散文出版过一次。《虚土》是我写的非常喜欢的一本书,既像小说,又像散文,但我觉得它更像诗歌。我写那本书时找到了一种诗人的感觉。
当然,《捎话》这本书就是纯粹的小说了。尽管有文体上的跨越,但从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开始我所营造的那个文学的世界,在这本书中还是得以延续,那样一个灵性世界,那样一个观照了人和人之外世界上所有的声音的世界,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完整的、系统的、完美的呈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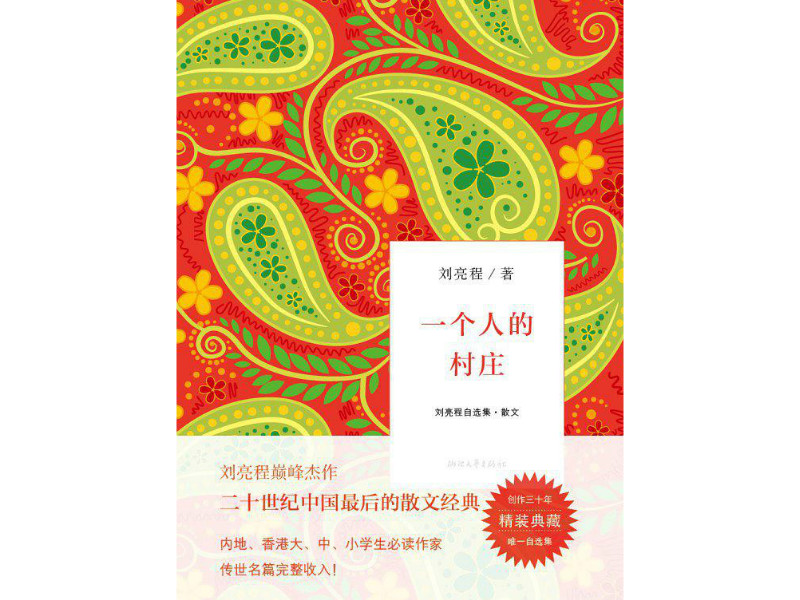
《一个人的村庄》 作者:刘亮程 版本: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年10月
新京报:你的写作一直关注乡村,关注自然,你如何看待城市写作?
刘亮程:每年都有那么多长篇小说被写出来,大部分还是乡村题材。可能有一些青年作家,涉猎城市题材的比较多。城市经验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积累。尽管我在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,城市对我来说可能还是陌生的,我可能还是没有从心灵上接受城市。但我想,有关城市的文学作品肯定会越来越多,因为这个城市家园,终有一天也会收留我们的灵魂。
新京报:乡村或者自然,对你意味着什么?
刘亮程: 乡村是我把半生扔在那儿的地方,是我的祖先千秋万代生于此死于此,并将这种生活文化传递给我的地方,我在那儿获得了成长,获得了看这个世界的眼光,获得了所有早年的生命体验和记忆的地方。而那个乡村又天然地在自然之中,所以到目前为止,我只能去写那个在自然中的乡村。
新京报:建立了一个木垒书院,是基于怎样的想法?对它有怎样的希求?
刘亮程:当时在村子里买了一个老学校,原计划是在那儿养老的。不是还没老嘛,老还要再过一些年,不能闲着,就做了一个书院。做书院也是中国文人的情怀。我们古代的文人,凡是有点想法、有点能力的,老了都会做一个书院。或者开一个私塾,带几个学生,或者开一个书院,做一个道台,带一些弟子,坐而论道。这是中国文人的情怀。我们那个书院也是这样,尽管也没有真正发挥一个书院的功能,每年有一些文学和艺术的培训,更多的时候只是作为一个个人生活的场所。
新京报:看来你对中国传统文人的作风是向往的。
刘亮程:是的。我想,不管我们生在多么现代的社会,随着年龄的日增,它(传统)有一种吸引力,会把我们吸引到古代文人的那种生活和理想情怀中去。我不见得会完全接受他们的思想和精神,但是,肯定跟他们有心灵和情怀上的联系。你会天然地觉得,你会跟着他走,这条路符合你的精神追求。
选自《新京报》网
|
Copyright © 2015 西部散文学会 Power by www.cnxbsww.com 

地址: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|